專題:“特朗普2.0時代”正式開啟!不會立即征收新關稅?非美貨幣狂飆!
2021年1月,“國會山騷亂”事件震驚全美,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黯然退場。彼時無人料到,四年后特朗普會卷土重來,高通脹下底層民眾的不滿讓特朗普成為美國第二位非連續執政的總統。
當地時間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他發表了為第二個任期奠定執政基調的就職演講,誓言要美國利益優先,為美國開辟“黃金時代”,打擊“激進、腐敗的建制派”,同時赦免了約1500名“國會山騷亂”暴力分子。
驢象兩黨愈發激烈的博弈成為美國政治極化的生動注腳。特朗普撤銷近80項拜登政府的行政命令,實施聯邦法規凍結以控制官僚體系,解雇部分不合格聯邦官員并暫停國稅局新員工招聘,要求全職聯邦工作人員返回辦公室現場辦公,加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以降低能源成本,結束聯邦政府對公民的言論審查,取消拜登期間將古巴移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的決定等。
引人關注的是,特朗普在關稅、俄烏沖突等問題上刻意模糊,“特朗普交易”遭遇逆轉,美元大跌,非美貨幣大漲。雖然特朗普的“變臉”有些意外,但其實一切都在情理之中,競選時期的戲劇性口號“功成身退”,上任之后特朗普必須轉向務實。
隨著特朗普2.0正式拉開大幕,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已經浮現:特朗普如何在重重阻力中推進經濟政策?歸來的特朗普能否“讓美國再次偉大”?
新官上任三把火
正如此前的“預告”,特朗普“新官上任三把火”燒得格外旺盛。
上臺首日,特朗普簽署了一系列行政令,其中包括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宣布南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并派遣軍隊抵御所謂非法移民“災難性入侵”;宣布國家能源緊急狀態,加大傳統能源開采,結束拜登政府“綠色新政”,撤銷電動車優惠政策以拯救美國傳統汽車工業;建立對外稅務局,對外國進口產品加征關稅;宣布美國政府將只承認男女兩個性別;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將擴張美國領土,把美國國旗插上新的地平線;將把美國宇航員送往火星。此外,特朗普宣布將從2月1日起對從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的商品征收25%的關稅。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典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以高調的“緊急狀態”開局,圍繞移民、能源和經濟等核心議題推出了一系列激進政策,試圖通過危機治理和權力集中,快速推進自己的施政目標,同時將民族主義與經濟保護主義作為政策基石。這些優先事項短期內可能提振經濟和增強其支持者的信心,但從長期來看,潛藏著巨大的社會撕裂、國際孤立和民主制度削弱的風險。
從領土擴張到火星計劃,再到治理架構的重塑,表面上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充滿激情與雄心,但背后充滿了實際執行的難題和潛在爭議。劉典認為,這些提議更多是服務于特朗普個人政治形象的象征性政策,而非完全可行的戰略規劃。
另外,特朗普在非特殊時期,宣布國家邊境緊急狀態和國家能源緊急狀態意味深長。在劉典看來,特朗普精準抓住了美國人對“危機”的集體焦慮。從通貨膨脹到移民問題,再到能源短缺,他以極具煽動力的語言將這些問題描述為對國家生存的直接威脅,并用“腐敗的既得利益集團”作為矛頭所向。“他們攫取了權力和財富,我要將這些奪回來,還給你們——真正的美國人!”
乍一聽,這似乎是一場針對腐敗的正義行動,但仔細推敲,劉典認為這更像是特朗普為權力集中所布下的棋局。他不僅要解決問題,還要確保整個過程完全掌控在他手中。比如特朗普提到要新設一個“政府效率部”,名義上是為了解決官僚冗余,實際上卻是進一步強化總統權力,確保政策執行不被掣肘。
在劉典看來,特朗普的姿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以往的“進攻者”形象轉向了“掌控者”的角色。如果說他在第一任期更多的是對體制發起猛烈抨擊,那么這一次,他試圖通過制造危機感鞏固自己的權威。他的邏輯很簡單:通過塑造“只有我能解決問題”的形象,讓每一項政策顯得迫在眉睫、不可或缺。比如他宣布南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并將非法移民稱為“災難性入侵”。這是他競選承諾的延續,但更是危機管理的一個典范。通過把問題形容得越嚴重,特朗普在決策中獲得的自由度也越高,反對聲音自然也會被削弱。
得與失
對于特朗普而言,一系列強硬的政策并非沒有副作用。
例如,在能源政策上,特朗普再次打出了“緊急狀態”的牌。他明確宣布國家進入“能源緊急狀態”,稱拜登政府的“綠色新政”是“對美國經濟的致命打擊”,并承諾立刻撤銷電動車優惠政策,大幅擴大傳統能源的開采。他強調,美國需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氣的巨大儲量重新填滿戰略儲備,并以此作為重振制造業和出口經濟的核心戰略。
回歸傳統能源能夠在短期內提振相關行業的經濟表現,同時進一步鞏固特朗普在保守派選民中的支持率。但劉典提醒,這種激進轉向也可能帶來嚴重的環境后果,并使美國與國際社會在氣候議題上的分歧進一步加深。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用“緊急狀態”包裝能源政策,為自己繞過國會直接推動這一戰略提供了合法性,但這也意味著更多權力被集中在總統手中,未來的政策平衡或許將被打破。
特朗普的危機治理模式不僅是在政策執行層面“快刀斬亂麻”,更是一種對民眾心理的把控,他通過塑造危機感,將問題簡單化、迫切化。
危機治理雖能贏得短期支持,但其長期風險不容忽視。劉典警告稱,無論是移民問題、能源政策,還是治理結構的調整,特朗普的政策大多以犧牲協商與平衡為代價。如果危機成為治理的新常態,政策執行的空間雖被打開,但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更多的社會撕裂、國際孤立以及制度穩定性的削弱。
“大考”剛剛開始
在上任前,特朗普喊出了一系列豪言壯語,但就職伊始的政策實際上更為克制,關稅、俄烏沖突等問題僅給出了模糊的表態,特朗普沒有祭出大規模關稅,也沒有重提“24小時解決俄烏沖突”。
特朗普對關稅問題的“隱退處理”尤為顯眼。在競選時,他曾多次放話,要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10%的關稅,對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征收25%的高關稅,并成立“對外稅務局”,專門負責重新改造美國的貿易體系。然而,在就職演講中,關稅幾乎只是一句帶過的“保護美國工人和家庭”。這一明顯的語調轉變,并非特朗普突然放棄了他的保護主義立場,而是他有意將這一議題擱置,為后續的外交博弈留下操作空間。對于特朗普來說,關稅不僅是一種政策工具,更是一個談判籌碼。他可能希望通過保持模糊,在未來的國際談判中靈活使用,用關稅施壓以換取更有利的條件。
事實上,關稅在特朗普競選期間發揮了更大“口號”作用,而進入實際執政階段,特朗普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民主黨政府因高通脹陰霾被選民“拋棄”的教訓還歷歷在目。
在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看來,就當前民調來看,關稅不是美國選民的核心議題,且潛在的再通脹壓力也對關稅政策形成制約。大規模加征關稅可能對通脹產生較大上行壓力。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測算,如果美國對所有國家加征10%關稅(假設不存在貿易對等報復),可能會對2025年美國通脹形成0.64%的上行影響;如果存在對等報復,可能上升至1.34%。自2024年9月份美聯儲降息以來,美國CPI增速自2.4%反彈至12月的2.9%,對特朗普關稅政策形成掣肘。從非制造業PMI物價指數等領先指標來看,CPI未來仍有進一步上行壓力。
展望未來,李超認為,特朗普短期新政可能優先關注國內民生問題,除了移民、油價議題外,短期和民生息息相關的財稅議題也有較高重要性,當前美國國內財稅問題隱患仍存。
財政預算問題方面,美國2025年財政預算并未通過,當前以“臨時預算(CR)”方式維持政府運轉。拜登在去年12月21日簽署了當前臨時預算案,有效期至2025年3月14日,意味著特朗普需要協調國會在3月14日前通過新的預算法案以防止資金中斷。
債務上限問題也再度逼近。2023年1月,美國達到了31.4萬億美元的債務上限,國會立法將債務上限擱置至2025年1月。截至1月16日,美國未償公共債務總額達到36.2萬億美元,約束回歸后美國財政部將進入“債務發行暫停期(DISP)”,使用公務員和郵政服務退休基金、財政部外匯穩定基金、財政部現金余額(TGA)等資源來臨時提供政府支出。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1月16日的報告顯示,應急手段或將在2025年第二季度耗盡,美國財政部將無法履行其支出義務。
更重要的是,減稅是特朗普核心政策主張,其2017年《減稅和就業法案》中大部分條款將在2025年底到期。由于上述法案需要國會的參與,而共和黨在國會立法優勢并不明顯,二季度前將這些法案通過“和解”程序打包通過可能是特朗普的最優先事項。
“讓美國再次偉大”挑戰重重,前路特朗普仍有諸多難關待闖。從政治層面來看,“打破規則”的特朗普已經重塑了美國,但在經濟層面,特朗普面臨更大挑戰,真正的“大考”才剛剛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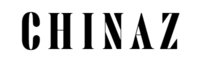






 冀ICP備15027495號
冀ICP備15027495號